由於歷史因素,巴爾幹半島最著名的城市也許就是薩拉熱窩。1992-95年,市內每天都有炮彈攻擊,宗教與種族問題奪走了無數生命。
Sarajevo meeting of cultures
在薩拉熱窩的舊城區購物大街上有一條白色線,線的一面建有橫七豎八的土耳其建築如清真寺、小攤賣的是土耳其精品和食物。
越過了白色線的另一面卻是全歐式的:雕花的窗戶、五顏六色的油漆塗在小小的三四層洋房上充滿喜感。難怪薩拉熱窩成為兵家必爭之地,這富饒的小城既有幾百年間鄂圖曼土耳其建下的亞洲輝煌文化、又有奧匈帝國留下的西歐近代文明。
古城有一條河,好像叫Latin River。橋的一端有一所小小博物館。這夾角的小房子,今天正好泊了一輛車子。這個位置就是當年奧匈帝國王儲被塞爾維亞19歲青年學生暗殺之地。奧地利要塞爾維亞交出學生,塞爾維亞不肯;奧地利攻擊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向俄羅斯求助;德國、法國、英國魚貫入戰場,由暗殺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戰只有三十七天。
不足兩個月前的2014年6月28日,這裡有很多遊人來憑弔一戰;其實有熟讀什麼Triple Alliance VS Triple Entente的學生們都知道,大戰一觸即發,早因為有民族主義、軍備競賽、秘密條約等等遠因。一戰是終歸都會發生、不可逆轉的人類歷史悲劇。打完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薩拉熱窩人的苦難還未有遠結。流行曲《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茱麗葉》的真實故事
前南斯拉夫解體時期薩拉熱窩遭到了44個月圍城之役,90年代香港人熟悉的流行曲《薩》就是改編一套外國同名紀錄片的作品—那位塞族青年和回教的波斯尼亞女郎,其實是中彈兩天躺在橋上失救而死的真人真事情侶。這間佈滿彈孔的小屋,今日成為了博物館。屋下的地底通道只有1.6米高1米闊,20年前物資和槍械就靠這小通道運送。閃身入內亞洲女性的筆者尚且感到窄狹黑暗,試想想軍人和平民在倉皇逃生時如何在這環境下爭取最後一線生機。
這幢小屋現在已經成為了歷史博物館。裡面展出的是當年戰爭留下的物資。1968年的罐頭、1937年的餅乾,通通是1992-1995年間薩拉熱窩人的食物!這些食物,竟然還是聯合國提供的!吃這些會不會食物中毒死?欠缺煙囪的火爐,冬天時窩在室中使可會中一氧化碳毒而死?就當你福大命大了,當年十二三歲的少年(假定和筆者同年的孩子)冒著槍林彈雨去取水回家,是多麼可怕又讓人肅然起敬的勇氣!
回想在街上看過一些和自己年紀相近的薩拉熱窩青年。也許他們沒有我們新潮、玩得,他們卻在最重要的幾年成長期時經歷了危城四十四個月戰後餘生。那眉宇之間的成熟、睿智和淡然,不是那些向來只關心搶不搶到iPhone去先達炒第一水、星期六日去哪裡High Tea或者限定化妝品買不到了的香港青年男女可以比擬的。
我們沒有什麼了不起,不過是投胎在太平盛世而已。你生存著苦苦工作的今天,是你小時候日哼夜哼的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茱麗葉兩位主角盼望不到的明天。
一城山色半城湖
下午離開薩拉熱窩到波斯尼亞第二大城市莫斯塔爾(Mostar)。車行十幾公里,只見環吾皆山,林蔭蒼蒼綠水淙淙,偶爾一座清真寺或一座教堂,啡紅色磚塊的小屋煙囪噴出煙霧,老婦坐在花園玫瑰邊小睡,身邊又是一座爐,嗯,他們都喜歡烤羊肉。
除了看風土人情,在車子穿過山巒時看到很多罕見又大型的大自然奇景。造山運動把水底的陸地谷上地面,層層的摺紋如同風琴。誰說坐車是補眠的時間?Window Sight-seeing,是最短時間把新地方景色收盡眼底的方法。
薩拉熱窩,是筆者真心要向各位推介的人生必到地。巴黎鐵塔或倫敦橋能讓你在朋友前炫耀到過「歐洲」;薩拉熱窩的鮮血卻滲在骨子裡,每一個遊人都能用悲痛心情、身心撕裂地體會世界和平不是無聊的生日願望,而是人類的永恒祝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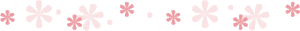 申請日本Telecom Square的Wifi 可供多人同時使用!Telecom Square是日本公司,使用Softbank或Docomo 4G網絡暢通無阻~
申請日本Telecom Square的Wifi 可供多人同時使用!Telecom Square是日本公司,使用Softbank或Docomo 4G網絡暢通無阻~
http://www.telecomsquare.hk/kiris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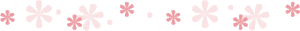
訂閱Blog主臉書: http://www.facebook.com/kiri.c.wong
關注Blog主微博:http://weibo.com/wongkiri














